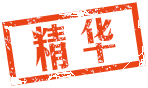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一壶漂泊 于 2010-3-23 17:36 编辑
昨日,父亲从乡下来看我,拎着一株黄泥头拱。 黄泥头拱就是春笋。不过,一般的春笋是没有资格被称为黄泥头拱的,一定要深厚的黄泥土壤,在清明谷雨时分,不露出泥土的春笋才算。不过,也不是绝对的,还要因时因地而异。 我一直以为,寻笋与钓鱼差不多,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。我的家,在铜岭岗的烟厂,地质的基本特征就是黄泥夹杂铜板石.黄泥层极厚,典型的酸性土质,特别适合竹笋的生长。惊蛰的隆隆雷声过后,伴随着绵绵春雨,笋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上串。于是,看地势,察裂纹,轻刨细挖,就能看到金黄的笋尖从同样黄的泥土里冒出来,那种兴奋的感觉是很难言表的,我小时候常以 “哈哈,又一株”表达。 我到现在还能记住的黄泥头拱只有一株了。那是在小满时分挖的。村里的李姓人家因造新屋,将黄泥填到竹园里,极厚极厚。一般来说,节气到小满时分,所有的笋早已出齐,春笋已成新篁了。可因为李姓人家的填土,又填的皇帝他妈——太厚,这片竹林竟没有一株笋冒出头来。我那时约莫10来岁,对寻笋这档子事还是颇有心得的,看那几株毛竹叶子茂密,毫无疑问是大年竹,就不相信这样的竹林居然不出笋,于是很不死心地天天转悠,历时一月有余。 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。那天日落时分,我又在那块竹林转悠,突然发现有一块土凸起,裂纹呈放射状,于是拿起锄头去轻刨,就这么几下之后,赫然看到一个澄黄澄黄的笋尖,呈弯曲状,笋尖紫嘟嘟的。凭我的直觉,这是一个超级大家伙,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多大,只清楚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。 笋尖朝向斜坡一面。这是一个好迹象,说明不用太费力。于是开始刨土,追随着笋纵深下挖,又纵深下挖。我已累得满头大汗,那个坑已与我的个子差不多平齐,可我发现,这株大笋起码还有一大截在地下!对山上人来说,寻到大笋却只挖到半截是不能被容忍的,要被人讥笑为“屙包”,少年气盛的我岂会善罢甘休? 只有继续挖。要深挖就必须把坑搞大,所谓唯有博大才能精深。问题是,身单力薄、腹饥难耐又兼天色渐暗,我急得差不多就想哭。这时,我听到有人大声呼唤我的名字,是父亲! 父亲在离家三十里的地方工作,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我的父母,是标准的严母慈父,打骂管教的事基本上是母亲包办的。父亲在家的日子少,与我们说话也总是用他教书先生和颜悦色的口吻,循循善诱,不过我总觉得生份,因此我在感情上一直不太接纳他,只把他当作一位长辈、亲戚或老师看待,更不会在他面前示弱或撒娇。 天差不多全黑了。我满头大汗,脸上全是黄泥颗粒,几乎看不清父亲的面容。幸好,他提了盏挈灯,向我挖笋的方位走来。“这时节还有介大的黄泥头拱?歇一下,我来挖。”父亲察看了“笋势”,从我手上接过锄头,认真挖起来。毕竟是大人,力气跟经验都不是十来岁的我可以比的,没费多少工夫,一株跟他差不多高,跟他的腿差不多粗的黄泥头拱,终于出土! 这笋可能有二十多斤。父亲说,这是他见过最长最大的黄泥头拱,我说我也是。那一刻,我既疲惫又满足。为笋,更为父亲。我终于知道,父亲就是父亲,不但有能力帮助我,更是可以亲近的。 我扛着锄头走在前头,父亲扛着笋提着灯走在后面。灯光照着前方的路。家,越来越近了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