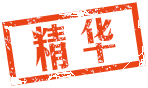|
1992年夏,宁海海带滞销。友人提供信息说:沈阳的价格不错,于是在峡山的白石岛收购了50吨,到宁波北站装上火车,往沈阳发货。 作为商人,我的胆子算是大的。因为有过几年闯荡江湖的经历,即使孤身一人到从没去过的东北,也觉得理所应当,逐利而行嘛。怀揣付完海带款及火车运费后剩下的一千元钱,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,终于在一个叫苏家屯的站下了车。 苏家屯是沈阳的一个区,离沈城尚有十五公里左右。阡陌交错,稻田鱼塘,一派江南郊区景象。我那时的普通话基础极差,面对这里的人往往不知所措,听他们说话也不知所云,因此沟通起来颇为吃力。经多方打听,终于在一个叫大淑堡的乡镇找到一家可以屯货也可以住人的店,价钱不算贵,一个月800元,而且离火车站才5公里路。 屯完货付了钱之后,只剩两百来块钱。我知道,自己陷入困境了。提供信息的朋友不了解8月初的东北。黑土地长出来的瓜果蔬菜好吃又便宜,人们根本不需要海带!只有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,蔬菜逐渐短缺,只剩下土豆白菜的时候,人们才吃这玩意儿。也就是说,要到十月初海带才可能动销,将近二个月的时间里,海带根本就卖不动!这与价格无关,而是来错季节了。 心,拔凉拔凉的。咋办呢?要不了一个星期,我将身无分文。没有亲戚朋友,没有熟人老乡,甚至没有一个说江浙口音的人,任何求助的渠道都没有。向家里或家乡的同学朋友求助是不可能的,我那时是宁肯活受罪也死要面子的个性。试图零售海带换点生活费,谁知骑了一天的“倒骑驴”沿村叫卖,根本就没人理,就算白送都没人要!人们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这个不识时令的异乡人,也许他们在想:这个南方小伙子莫非脑子有毛病,是个标准的“二百五”? 五天之后,口袋里的钱只剩下五十元,如果再找不到活路,我将成为沦落异乡的乞丐!即使每天稀饭馒头加大酱,也撑不了几天的。没有任何办法,只能硬逼着自己骑着“倒骑驴”去走街串巷,期望淳朴的东北人同情一下我,买去一斤二斤的海带。 八月初的沈阳同宁海一样的热,特别在中午那段时间。我热汗涔涔,腹饥口燥,骑到一户院子里有颗大枣树的人家,想歇歇脚,顺便讨口水喝。树荫下,一位五十来岁的汉子躺在凉椅上,正戴着眼镜看一本书,书脊上竟赫然写着《权力意志》!我的天!一个乡下的农民,竟在看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作,这是何许人也?一年前,我也曾看过此书,晦涩难懂得很。 他让我坐下来,起身到天井上取水。此地的水井是封闭在地下的,取水时只需摇动一个扳手一样的东西,清凉的井水便汩汩流出。没有细菌污染,可以直接饮用。接过他递过的水勺,一阵牛饮之后,沁入肺腑的滋润便向全身漫延。我长舒出一口气,同他聊了起来。 话题当然是从尼采开始的,慢慢地就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了。那时,我自诩为商人中的文人,骨子里是很傲的,尽管做的是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意。让我惊异的是,他的知识面极广,似乎我知道的他全都知道,还有很多我不清楚的地方,他只是笑笑没有说出来。不过我感觉得到,他其实是知道的。可能是交浅不宜言深,他不想在我这个小辈面前卖弄而已。 他告诉我,他姓阮,让我叫他老阮。祖籍是宁波的,小时候父亲当兵来东北,他是听着父亲的甬江牌普通话长大的,因此对我的所谓普通话不但全都听得懂,还有一些亲切感。他初中毕业时,父亲因政治运动冲击,被下放到村子里,没几年就辞世了。他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十多年,娶妻后生了二个女儿,一直安份守已地当农民,没有出过远门。“阿拉阿爸话,走遍天下,勿如宁波江厦!”老阮迸出一句还算道地的宁波话后,哈哈大笑,问我讲得像不像? 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虽然谈不上他乡遇故知,还是有一份乡情在里头的。于是,我向他讲述了我的困境,希望得到老阮的指点。我当时的确没有想他能帮我的,看得出来,他家的境况是相当贫寒的。二间平房一个炕,二口大灶几袋粮,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,更谈不上电器,典型的贫困农村中的贫困户。 老阮很认真的听着,皱着眉头叹了口气,“老弟!”他这样叫我。“你搬到我家来住吧!老哥家虽穷,大米饭有的是,饿不着你哪!你这么年轻,暂时落难,我们谈得投机,又是老乡,我不帮你谁帮你?只要你不嫌弃,下午就搬进来住!” …… 那天晚上,在老阮家的炕上,我盘腿面对老阮喝起了酒。酒是当地一种叫“老龙口”的白酒,45度,2块1一瓶,是老阮让他的大女儿从小店里赊的。菜有六碟,刀豆是院子里摘的,煮熟放盐,他家没有油。青椒和茄子都蘸大酱生吃,土樱桃也是后院采摘的。唯一的荤菜是一条鲤鱼,是他自己从弟弟家的鱼塘里捞的。还有一样东北人情有独钟的便是大葱了,可惜那天的大葱并不大,我也受不了那种冲脑门的刺鼻味,就敬谢不敏了。 他的二个女儿极讲规矩,分坐左右二旁。大女儿上高中,小女儿读初二,不声不响,都冲我笑笑,都叫我“叔”。看得出来,老阮对二个女儿是很慈爱的,尤其是小女儿。他将鲤鱼肚子上的肉剔去刺,放在小女儿的碗里,然后笑着看她吃,而女儿也报之灿然一笑。这令我动容,父女间的关爱流露得如此细腻自然,在这样的贫寒之家是很难得的。 那晚我就住在老阮家,同这一家四口合睡一个炕。我睡在远离灶台的最上首,这是对贵客的待遇。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,我无所事事地闲住在老阮家。白天陪着老阮到田埂上转转,逮一些蜢蚱或挖点泥鳅改善生活,晚上基本天黑就睡。偶尔也有几天凑凑热闹,跟着村里人上邻村去看戏,就是那种土得掉渣俗不可耐的二人转。 他们一家都没有拿我当外人看。同吃同住,没有客套礼让。唯一一件让老阮很生气的事,就是当我离开他家去沈阳城时,老阮发现:二个女儿的钢笔字都比他好,这让他很没面子,埋怨我不肯教他。其实我知道,他这是偷着乐呢。 权当回报吧。二个女儿学得认真,我教得也不赖,因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步明显。老阮不在的时候,她们都改口叫我哥了,这是老阮所不知道的。人在江湖,一切随缘。内心里的感激,是不必一下子就说出来的。我也说不出口,一句轻描淡写的“谢谢”是不足以表达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激的。我不想让如此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受到世俗和功利的亵渎。就这样埋在心底,任由它慢慢发酵吧。 老阮没有送我。由他的二个女儿代他送我到村口。秋风已经很凉,枣树上的大枣已成熟变红。海带动销的时节到了,我得离开这家人去做自己的买卖。“哥!你啥时回呀?还能教我不?”小女儿装作很无邪的笑着问我,依依不舍的神色还是没能掩饰住。大女儿很矜持地笑着,没有一句话,同她挥手的时候,我发现,她的眼中有晶亮的东西,在晨光中闪烁。 丁易 5月26日
|